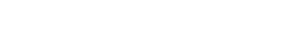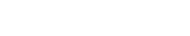中西对照视野中的潘公凯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新美术》主编曹意强教授专访
编者按:9月19日,在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美术学院、304am永利集团官网、山东省商业集团主办的“静水深流——潘公凯作品展”银座美术馆展厅,记者采访了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新美术》主编曹意强先生。
记者:您跟潘公凯院长有相似的学术经历,都是从美术创作实践领域起家,后来都转向了美术史的研究或者是教学工作,但是同时也都后来在创作领域进行思考和探索。另外您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生。在您的东西方美术史的研究视野里面,您怎么评价潘公凯先生的学术研究以及他在中国现代水墨创作领域所进行的探索?
曹意强:我跟潘公凯先生都是从创作转向理论研究的,我认为理论研究跟创作是两回事。潘公凯作为一个画家、艺术教育家,美术教育家,他做的贡献也是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他一直在探索中国画的现代性之路,重新思考中国画在世界艺术格局当中的地位。这种探索本身是一种在理论研究上的理想境界问题,潘公凯把对中国画的理解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但是艺术创作又属于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艺术史上的悖论。
记者:这个悖论指的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潘公凯理论研究的价值?
曹意强:我们都说艺术反映时代,也有人说艺术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我认为从中西方艺术史角度看,这种观点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是提升了个人的理想境界。为什么我说它没有实质的理论意义呢?是因为我们发现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民族的艺术,根本不用任何理论指导,它都会呈现它的一般性特征,比如说我们中国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它的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种艺术风格。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谈到艺术史本身的时候,它不是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一般性风格组成的,而恰恰是由那些完全跟这个一般性风格格格不入的、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创作构成的,他们的成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美术史。
当我们谈到理论的时候,不要指望理论一定能够指导实践,更不要指望我们提出某种理论将会预测艺术的走向。艺术是我们人类创造里面一个根本无法预知它走向的一种人类创造的产品。潘公凯在研究中国现代艺术之路的时候,他主要是提醒我们要在思想境界上努力地创造,发展我们的传统,要让世界真正的理解我们中国的艺术。
记者:那您认为潘公凯先生水墨创新的意义在哪里?
曹意强:潘公凯个人的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里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笔墨,特别是焦墨,这个传统跟他父亲当时的尝试是有联系的。他另外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比较西化。虽然我们中国绘画以前也分梅、兰、竹、菊之类的题材,但是一个画家把他全部精力集中到一个母题上,这是西方比较注重的观念,比如说有人在画桃子,就经常画桃子,画某一种教堂的景象,就经常画教堂的景象。潘公凯的创作抓住一个母题来探索中国画的整体语言,这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就像他在理论上探讨中国艺术经过与西方艺术频繁接触以后,在多大程度上被世界所认可,这一点非常重要。
记者:结合潘公凯先生的绘画创作,您如何看待绘画的民族性问题?
曹意强:我们现在过多强调了绘画的民族性。当然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创造,但是我觉得一个伟大的民族,当你真正处于最伟大的时刻,是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也在谈世界艺术,并且也可以把世界艺术放到“神品”的位置上。张彦远从来没说,我们中国的艺术特征应该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没法预计艺术将来的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也许潘公凯的理论跟他的创作实践中间可能有些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当做一个艺术家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种探索是非常理性的,对中国的艺术在国际上的推广是有好处的,在理论探索上也是这样。我希望把潘公凯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探索分开来看,不要粘合在一起。我们中国需要像潘公凯这样在实践领域里面有深切体验的,同时又能够做好理论的人。否则有些空头理论误导绘画界,特别是国画界。
记者:您认为中国画界在理论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曹意强:现在中国画界出现的最大问题把粗俗当做大气,这就是因为某种理论误导。比如说西方艺术写实,中国艺术写意这样的观点,我们读读中国画论,里面写真、写实、师法自然的内容太多了。东西方由于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造成了中西艺术的区别,并不是说西方人的眼睛和手生来就是为了写实的。其实西方的艺术是从最“形而上”的理念升华,柏拉图说“现实是虚幻的”、“画家是最虚幻”的理论影响了整个西方艺术,柏拉图讲的“床”的故事,意思就是说画家就是欺骗人的眼睛。但恰恰就是这个理论刺激了西方所谓的写实主义的发展,很奇怪。
我们现在理论界的很多事,都需要不断进行深入思考,不能只是看表面的东西。西方艺术写实,中国艺术写意,这些观点都太肤浅,难道西方艺术不会写意吗?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西方就提出来最好的艺术就是那种轻松自如、意到笔不到的作品,所以后来西方油画也是越来越讲究表现力,一直到抽象表现主义为止,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好好研究。我觉得潘公凯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真正了解了西方。
记者:中西艺术交流中,双方如何超越文化背景的差异,更好的理解对方的艺术?
曹意强:我就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西方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但是当我们需要它作为我们某种支撑的时候我们就说西方有这个,其实西方没有这个;当你不需要的时候,或者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西方去,国画界就是这样的情况。从《历代名画记》推断,西方艺术至少比张彦远之前就已经介入了中国艺术了,但中国艺术还是朝着成为世界艺术一朵奇葩的方向发展。反过来说,西方人如果对中国绘画不理解,那很正常,问题出在我们,因为我们中国的学者没有做出像西方人那样能够把中国艺术推向世界的研究,能够教会西方人欣赏中国艺术、中国绘画。现在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参观画展,有人会笑话他们不懂中国艺术。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责任,就像我们如果不懂西方艺术是西方人的责任一样。西方人在西方艺术的推广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使西方之外的很多人了解到西方艺术。我们现在了解西方艺术史,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艺术艺术史的了解,这不是我们的功劳,是西方学者的功劳。
以前我在牛津留学的时候,我就写过一封信给一位著名的西方艺术史学者。我说我们中国艺术非常的伟大,但是光说它伟大是没用的,我们必须做出可以与他匹配的学术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艺术,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像潘公凯这样的艺术教育家,在这两个领域里面同时推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美术教育家,而且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学者型画家。这不是一个特例,中国历代都是这样。所以我说在济南举办的这个展览非常有意义。
整理人:马静 赵慢慢